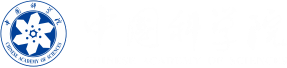我眼中的老科学家
我的父亲敖栋辉
时间:2022/10/27
虽然对农业育种工作没有深入的了解,但因为父亲长年所从事的工作,我也多多少少知道了育种是一项极其艰苦繁重,过程枯燥而周期又漫长的工作。选育一个小麦新品种,往往需要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头顶麦秸草帽,身着袖口磨白的工作服,脚穿陈旧的帆布鞋,在烈日下站在或青绿或金黄的麦田中,像极了一个川西平原上的普通农民。从小在我的脑海中,父亲的工作形象就是这样一幅画面。他一直说他就是一个拿工资的“农民”,只有把自己当成农民,才会真正爱上土地,爱上麦子,爱上育种这个艰苦的工作。
每年的五一、中秋、国庆这几个阖家团聚的时刻,也正是他们选育品种的关键时期,所以父亲和他们农业室的同事们这期间多半都是把农场当家。我妈曾说,那些田头的麦子就像是他的娃。父亲对他的麦子真的是比对我还熟悉,记得小时候他大多的时间都是在农场,对于我上几年级了他都搞不清楚。
父亲六十多年的育种生涯,基于一个最朴素出发点——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所以能够坚持这么多年,是缘于他对做事情的那股认真执着劲儿。他对名利一贯看得很淡,始终保持着一颗平常心。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当时所里刚恢复职称评定,正值他们选种的繁忙季节,他根本没把这事放在心上,他觉得有没有职称一点都不影响他在田间地头工作,先把眼前的选种工作做好,静下心来搞研究最重要。眼看职称申报的最后期限就要到了,他还没有提交申请,他们室里的游书记急了,亲自追在他后面动员,甚至坐在我家里督促他填写申请表。
每年从麦田里站了一个选种季下来,父亲的一双手都被烈阳炙晒得漆黑脱皮,我妈戏称他:“刨碳花儿的又回来了。”就这样,几十年的寒来暑往,年年在麦田里站着、晒着,一晃人就老了。1998年,到了退休年龄,本以为他可以回来安心地弄他的那些花花草草,好好清闲一下了。可他仍然不肯停歇,还是一门心思扑在育种工作上。他说对于他,每到开春或是麦收时节,站在田间地头,看着麦浪翻滚,那才是一种真正的享受。
不服老的他,这一干又是二十多年。就在前年9月份时,他突患腰椎间盘突出,每次起坐都很困难。眼看十月的选种季就要来了,我妈心里又着急,又暗自有点高兴。着急的是他的病情,高兴的是:这都坐不得了,看他还怎么去马尔康下田,趁机就可以把他劝退了。哪知道父亲这回治疗自己很是积极,又是贴膏药,又是理疗。时间一到,他还是准时挎上他那个破旧的背包出门了。我们谁也劝不住。这两年,我妈常跟他说:“你喜欢是一回事,但毕竟八十多岁的人了,本身也有一些老年基础病,要面对现实,不能逞能,你要实在想继续做,就在办公室整理一下材料这些就算了,不要再出差下田了。如果你在外面出了什么意外,不仅自己受苦,也会给所里造成麻烦。”可他总是固执地说:“我的身体我自己心里有数,对小麦育种的来说,田地是最重要的实验室,也是所有努力的最终目标,不下田,还搞什么育种嘛?”
如今,八十四岁的父亲依然坚守在田间地头。在选育小麦材料的紧张季节,他和同事们一道经常一天在田里一站就是几个小时,连当地那些常年劳作的农民都自觉不如,对他佩服不已。唉!对他这个执着的老人家,我们也实在是拿他没有办法,随他吧,他就是那种典型的“择一事,终一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