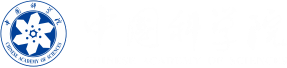【中国科学报】陈有华:算一算 更接近科学真相
时间:2024-01-31

陈有华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 杨晨
陈有华的书桌上,有一个A4纸大小的厚皮记事本。里面少有文字记述,更多的是一行行推导公式,或者折线图。
“像这幅图,就是我模拟的物种随气候变化的衰减趋势,然后再根据这个猜想,结合数据验证建立模型。”陈有华向记者介绍,这样的“草稿本”摞起来,足足有他半个人高。“从大学开始,我就有一边思考一边打草稿的习惯,写下来,学术思路会更清晰。”
数学计算和推导是陈有华工作中必不可少的一环。他是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长期从事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统计建模这一细分方向研究,即将数理统计方法融入多样性研究,让复杂的生态学现象与过程描述更定量化。
虽然草稿本里大部分推算以失败告终,但陈有华坚信,科研的本质是追求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路漫长且曲折,靠的是坚持。”
寻真相 把生物多样性研究“定量化”
在广阔的生物界,繁衍着丰富多彩的动植物。但在陈有华的视角里,这个世界就像一个沙盘,“小林子里,有两栖动物、爬行动物、昆虫,也有草地、灌丛和参天大树,偶尔有鸟群飞过。”而他要做的,就是俯身打量着沙盘的每一个角落。
以生物学为基础,他着眼多样性研究,将涉猎的领域拓展至生态学,并深入探讨生物与环境的关系。
“然而这个过程中,光靠观察和实验还不够。”他在对宏观生态以及进化保护的研究中引入了数理统计学的方法和理论,尽量让生物多样性研究更加定量化。“有人会觉得,自己所收集的数据够全了,不必再去统计和推断。”但陈有华坚持认为,所有的自然科学研究都有不确定性。
地球探测卫星的视角再广,也无法完全看清地面每平方米内的每个物种个体;红外相机的安装尽管为野外调查提供了极大便利,但也存在可靠性问题。“这些还是得靠数学统计帮忙回答。”陈有华说,即使实验控制得再精妙,测量误差永远存在。而数理工具的运用,就是让结果更精准、更逼近科学真相。
最近,他从艾伦 图灵密码学理论中获得灵感,基于泊松分布开发了一个简单的估算工具,用于预测野外调查中发现单个新物种的最小距离。“物种的分布一般受其生物学规律和人类活动的影响,但此次研究设计的估算工具纯粹是从数字中找规律,是分析了一系列调查数据后开发的模型。”他正着手将这一模型升级,提高野外调查的成本效益。
烂笔头 在“打草稿”中拨云见日
生物多样性的研究被认为“很抽象”。“但我做的,就是从抽象到具象,从宏观到微观,探讨一个又一个具体问题。”在陈有华眼中,一个区域内的调查数据不仅呈现的是个体数、形态特征等信息,还隐藏和反映了多个生态学道理,例如物种共存、性状替换或区域内资源承载力等。
“我可以针对一组数据问无数问题,思考的过程也是将抽象‘落地’的过程。”提出问题后,陈有华就用数学和统计的知识去解答,化成笔下一个个公式。针对一些特定问题的解答,如果没有现成的模型或方法,就得自己去构建。
平时,陈有华喜欢走路或坐地铁上班,因为这一路上他有足够的独处时间和精力去思考。陈有华的书桌上,总会准备一个笔记本,有了点子就进行笔算。向上或向下的变化曲线预测、一步步连贯的推导过程,都在一页页纸中肆意呈现。
陈有华一坐就是大半天,虽然总是提醒自己要按时吃饭,但不想灵感被打断,因此宁愿错过饭点。头脑风暴又很费脑,所以陈有华喜欢吃重油重盐的食物,他常自嘲“过劳肥”,体形管理不太理想。
在草稿本上天马行空的时刻让陈有华极为享受。最近,他正在研究“生境到底损失到何种程度才会导致物种灭绝”这一问题。从群落分析的角度,他抽丝剥茧,推导出一个大致的公式。“当一落笔,一切‘化繁为简’、拨云见日时,感觉太美妙了。”
数理统计学毕竟不是陈有华的专业,所以他一边自学相关理论,一边寻求跨界合作。“毕竟这项研究工作开始会很抽象,我自己要思考,也要说出来,和他人讨论获得更多启示,就算偶尔产生分歧也无所谓。”
如今的科学领域更加细分化。“就像大树的根一样,尽管细,但相互关联,共同撑起大树的枝繁叶茂。”
行千里 勇于闯入“无人之境”
做研究,“纸上得来终觉浅”。陈有华不仅要埋头写,还要行千里路。“无论是生态学,还是生物多样性研究,分类学都是基础中的基础,这也意味着野外调查的重要性。”
一年中不少时间,陈有华的课题组都会“泡”在野外,毕竟实验和论证所需的数据大多需要采样来获取。看生境、做样方、走样线、查物种、做记录……野外跑得越多,陈有华的思路就越开阔。
不久前,陈有华和不同领域的研究人员一同到贡嘎山做生物多样性与地质多样性调查。受前年地震影响而闭园的海螺沟景区刚好恢复开放,一行人直奔冰川深处。
越往里走,越难见人迹。当他们决定顺着曾发生过滑坡的山体往下走时,同行人有的担心风险而止步,陈有华则与上海一位做应用数学的学者继续前进。
“到了山体底部,我们发现了一些比较奇特的地质地貌,拍了不少照片。”陈有华觉得,这一趟来值了。这就是科研的意义:勇敢去闯无人区,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
“我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就好像一个‘无人区’。”陈有华说,数理模型的搭建往往比较复杂,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最终得出的研究成果,一时也不可能彻底解决什么实际问题。”
他对科研的信念,就是更好地认识自然,为保护生态提供数据支撑。这几年,陈有华取得了不少科研进展,有的证明了全球林栖脊椎动物的“灭绝债务”始于第二次工业革命伊始,有的厘清了全国两栖动物多维多样性空间格局,并提出了一系列保护优化措施……
“尽管目前的研究仍处在一个‘量变’的过程,也许我终其一生,都达不到‘质变’,但只要对他人的研究,以及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有所启发,我就很满足了。”陈有华坦然地说。